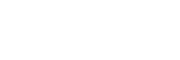文化教育如何弘扬?我们需要怎样的传统文化教育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需要弘扬?
这是一个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讨论的问题,大多数人对此都不难给出一个或是或非的回答。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有多少人能够自信地说,自己确实了解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
去年我带学生参加了大陆与台湾合办的“国学夏令营”,很多学校都在夏令营中展示了本校开展的各种传统文化活动,然而仔细看来,其中有多少不只是拍照式的集锦?举行一场祭孔典礼、办一次书法比赛、甚至放一次风筝,都被冠上了弘扬传统文化的名号,这实在不能不让人觉得有些啼笑皆非。而我想说的是,这种种啼笑皆非的现象,其实从特定的角度而言,恰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不缺的就是作秀、最不缺的就是借由某种冠冕堂皇的口号或旗帜来抬高自己的行为艺术,这一点到今天也别无二致。即以读经而论,现在很多社会人士都大力呼吁要让四书五经进入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我并不否认其中确实有真正为文化发展而奔走呼告的有识之士,可我只想问一句,提倡读经的 诸位先生,你们觉得自己读懂了四书五经了吗?哪一位支持四书五经进入课堂的老师愿意告诉我,您准备如何在课堂里讲授四书五经?如何能够使得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真正起到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热爱中国文化传统的作用,而不是使学生学生在枯燥的文言学习中更增对传统文化的反感、或者甚至从我们的各种经典中学到所谓的“厚黑术”?
当然,我并非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但是首先我希望提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诸位先生能够真正懂得,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弘扬的独特的核心价值究竟在于何处。对于这方面的了解,余英时教授的文章《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是相当值得一读的,这篇文章曾被誉为“即使不是百年来中西文化论辩最后的断案,至少也是五四以降所有讨论文字中见解最圆熟、立论最透辟的一篇。”该文中有一段话对中国文化的正面价值评价得非常到位:“《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段话大致能说明内倾文化(即余英时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定性)的特性所在。这里止、定、静、安等本来都是指个人的心理状态而言的,但也未尝不适用于中国文化的一般表现。18世纪以来,‘进步’成为西方现代化的一个中心观念。从‘进步’的观点来看,安定静止自然一无足取。黑格尔看不起中国文化的主要根据之一便是说中国从来没有进步过。‘五四’时代中国人的自我批判也着眼于此。我个人也不以为仅靠安定静止便足以使中国文化适应现代的生活。中国现代化自然不能不‘动’、不‘进’,在科学、技术、经济各方面尤其如此。但是今天西方的危机却正在‘动’而不能‘静’、‘进’而不能‘止’、‘富’而不能‘安’、‘乱’而不能‘定’。最近二三十年来,‘进步’已不再是西方文化的最高价值之一了。……现代生活中物质丰裕和精神贫困的尖锐对照是有目共睹的。存在主义所揭发的关于现代人心理失调的种种现象如焦虑、怖栗、无家感、疏离感等,更是无可否认的。如果说在现代化的早期,安、定、静、止之类的价值观念是不适应的,那么在即将进入‘现代以后’的现阶段,这些观念则十分值得我们正视了。”
我始终认为,“国学”之根在于“学”而不在于“国”。并不能因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先天具有值得弘扬的价值;恰恰相反,正因为它有相对于西方文化的独特的精神价值,所以我们才因其产生于中国而感到自豪。确实,作为教育者的我们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时应该带有一种文化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并不在于传承“中国”的文化,而在于传承中国的“文化”。因此在我看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便首先在于理解余英时教授的这篇文章,并以此为锁钥,进而认真研读各种经典文本,从中获得一种文化方面的真正自信,由此最终达到一种教育上的可能。否则,事实上得到充分弘扬的便很可能只是传统文化中的功利传统、作秀传统——这一点是必须引起我们警惕的。
二
我在这里并不想继续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没有能力比余英时先生谈得更为深刻——而是希望将视角转向我们的基础教育,谈一谈传统文化(自然是指传统文化正面意义上的核心价值)教育是否能够在如今的教育体系中、特别是在中学语文教学的课堂上成为可能。
在现有的中学语文教学中,最能体现传统文化教育的部分自然应该属于文言文和诗词了。然而环顾现实中的语文课堂,有多少高中语文老师能够成功地让学生在除应付考试的文言知识之外对《报任安书》、《指南录后序》之类的经典篇目心有戚戚?对于古代文人来说,这些篇目之所以会成为经典,首先就在于作品中的情感对读者心灵的感发——古代的许多著名文人,往往会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而产生了一种对社会、对群体的疏离感,正是对个性的追求以及群体对个人追求的压制之间的相互作用,才产生了如此充满张力的经典作品。而与这些经典作品产生呼应的人是谁?自然也是历代那些具有敏感心灵的文学家。他们对作品的众多评论很可能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即经典作品在古代很受欢迎。但事实上,这些文学家相对于整个社会群体来说也仅仅只是少数。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情感永远只可能属于少数文学家,我只是很怀疑,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教学工作似乎在试图使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同时体会到这种对群体的疏离感,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古代少数人在其一生中某个特殊时机所体会到的感受扩展到如今整个受教育的社会群体,而且是在短短的几堂语文课上——这无论如何是一个极难实现的目标,放到任何一个时代,事实上都难以实现。整体而言,在如今的高中语文课堂中,对于作者在这些课文中所体现出的精神境界,大多数学生充其量只能做到“知道”,“理解”已是难事,更不必说“同情”和“景仰”。如果一定要让学生在回答问题时统一表现出对古人的景仰之情,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教学生如何说假话。
而诗词教学的情况也未必更好。能写出一篇像样的鉴赏文字的同学固然不少,但真正喜欢自己正在鉴赏的诗词的学生不多。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古代优秀的诗词缺乏魅力——在大多数学校中总有一些喜爱吟咏诗词的学生;然而无论在任何时代,真正一流的诗词往往总是属于少数的读者(即使是那些流传颇广的名篇,能够真正从内涵上深刻领悟其中意蕴并与之形成呼应的人也并不多)。倘若硬是要求让所有学生都能够与作者的心灵相呼应,那无论如何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目标,最终的结果也只是让学生学着鉴赏家说话,作出的鉴赏文字却远远不属于学生自己。
教导学生说假话,所谓“代圣人立言”,在很大程度上不妨也可以说是某种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倘若确实能够树立起一个高标准的文化标杆——也就是说,至少对于作者本人来说,他的文学创作是真诚的;对于鉴赏家本人来说,他们对经典作品的点评是到位的——那么至少对于各个时代少数的会心者而言,他们确实仍然有可能溯源追本,拨开迷雾直指本心。(在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化之后,仍然产生了朱熹、王阳明这样相对独立的思想家,便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如今更可担忧的事情却是,当我们寻找一个所谓公平的标准考查学生对古代文本的阅读水平时,最平庸的诗文、最为类型化的情感,反倒因为往往能表现出一种更为“理想”的考试区分度,而成为课堂训练的主要教学内容。(你能从这首作品中看出作者的惜春之情么?看出来了,好,答对了;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和“斜阳却照深深院”有何不同?因为牵涉到个性化的体悟,所以往往难以考查。)长此以往,那些具有相当文学敏感的学生,其文学敏感性就会日益钝化,终归平庸。同时,当我们力求尊重学生的自主解读时,对经典作品的庸俗化便也应运而生了。比如说《渔父》:很多老师在上课时都会引导学生就屈原和渔父的不同人生选择进行探讨,而在探讨中无论学生选择屈原或是渔父的人生态度,都会得到老师的肯定。然而,正是因为渔父的价值观也无法否认,才恰恰更好地映衬出了屈原对自己所选择的理想的执着坚持——“我承认,渔父的想法也许也是很好的,但是却不是我想要的”——这种近乎执拗的坚持,才更表现出了一种高绝的人格。倘若不能解读到这一步,那么这篇文章的价值又将何在?“屈原很傻啊”,“我更喜欢渔父,自己管好自己就行了啊”,这样的回答,在我们大多数的课堂上一定是更为常见的。而我们很多教师遇到这样的场合,往往就显得相当“宽容”——否则如何体现出尊重学生的多元性解读?更有甚者,如今一些标榜“创新”的老师,为了吸引学生的兴趣而主动肢解乃至曲解文学作品的内涵,以完全不顾作者的独特情感的方式任意拼接文本,这就更使得文化教育日渐平庸了。
总之我们不难发现,就现有的传统文化教育在课堂中的实现方式而言,虚伪和平庸,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两大痼疾。
三
从上面的探讨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在现有的中学课堂教学中,传统文化教育很难真正起到提升学生精神境界的作用,而且为了保证让所有学生达到一个对传统文化的平庸化的理解层面,却使得那些少数对传统文化有真正探究热情的学生也被拉低到同样的层面,由此,他们很可能会难以对传统文化产生深入的体悟和认知,并最终对探索传统文化的精髓丧失兴趣。倘若在这样的局面下急着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经典著作引入课堂教学,那么原本饱含先哲智慧的经典思想也很可能会成为一种似新而旧的令人反感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宗教还魂”。
那么,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是否就完全不可行呢?
可行。但前提是需要正视并承认接受群体的差异,破除将所有学生视为一体、将所有传统思想(即使是指那些最精华的部分)视为一律的认知误区,从而在不同层面上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有些传统文化教育应当落实为从早期教育开始的长期的耳濡目染,如孝道、如气节、如对宁静生活的喜爱,都可以通过各种历史故事、在各种与社会与自然的长期接触中得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家讲坛”虽然饱受诟病,但是其积极作用仍然是不容抹杀的);而有些传统文化教育,如思考抽象的哲理、体味细腻的情感等等,就必须要首先排除功利化的竞争思维,才能让思想真正成为思想。葛兆光教授在《中国思想史·盛世的平庸》中说过这样一段话:“狭窄的仕进之路上的竞争,使他们常常不得不一面对社会现实采取异常实际的态度,一面对官方意识形态采取协调的姿态,他们已经无暇思想,即使思想,也常常是本着实用的态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就只能越来越平庸了。”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思想从本质上而言应该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活动,我们当然应该希望、并努力使更多的学生喜爱这种精神活动,但是倘若在教学中要求每一位同学都必须参与这种精神活动,还必须用某种单一的考核标准来检验学生是否达到了一定的层次——那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思想被功利挤压得无从发展,整个社会陷入虚伪和平庸。
这就注定了思想层面的传统文化教育,至少从目前来看很难在课堂教学的大范围内得到普及。只有当学生在从小到大长期的熏染陶冶中较为普遍地获得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价值的一些初步认知和认同,在中学课堂教学中引入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经典才不至沦于异化。而在目前大多数中学生缺乏传统文化根基的教育现实中,在校内开设传统文化的选修课、开展研究传统文化的学生社团活动,或许是一种相对可取的选择。
我们苏州中学“钱穆国学社”就坚持举办着每周一次的读书会常规活动。作为一种自愿参加、师生平等、相互切磋琢磨的读书会,它不同于课堂教学中的教师讲授与学生听讲,而是以共同阅读经典、共同讨论经典为主要活动方式。在读书会上,时不时可以听到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激烈而愉快的争论,也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思维闪光点。而在这样反复的辩难当中,师生一起体会到了阅读经典的快乐:
“广博的学习,什么都懂,什么都不精通,这是‘不器’,但绝非‘君子的不器’。
“君子不器——成就通才,用无不周,君子应该是博雅的。但社会各方面的进步要依赖于有专攻的器皿,君子为实现个人社会价值必定要在某一时刻表现为某一种固定形态的器皿。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能够有多个方面精通已实属不易,怎么能指望一个人无所不通呢?当大器晚成时,人类寿命的极限又妨碍了他在最终选择的专业领域里更多发现,更多创造,更多贡献。那么,这样想来是否早点找准、认定专业方向,开小口,挖深井更好些?抑或对于成为一个高级单功能器皿来说,先成为一个万能器皿是看似无用费时实则必须的过程呢?
“器?不器?这也是困扰我自己很久的一个问题。目前还不能解决,也不用去解决,确实时机未到。总之,应该非常明确的是‘为己之学’的主张。当学习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时,什么专业,什么职业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这是某次读书会上,一位同学就《论语》中“君子不器”这一观念发表的独立见解。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读书会所探讨的内容并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经典文字,而是这些文字和每个人的人生的关系。当很多老师和家长都在为学生的阅读低幼化而担心的时候,苏州中学国学社的社员却已经手捧着各种人文经典,在讨论和交流中来思考、规划自己的人生了。我们的探讨并没有任何预设的答案,每位同学都畅谈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的独到见解,提出自己的问题,其它老师和同学则都作为平等的交流者,切磋着彼此的观点。由此,几乎每一次读书会后,都可以有几篇颇具水平的读书报告产生,其中的一些则被收入校刊,成为与全校师生共同分享的资料。
因此,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是否应当将传统文化教育引入基础教育,而是要首先明白应该向学生传播具有怎样价值的传统文化;不是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接受相同内涵的传统文化,而是要向不同层次的学生传授或浅显或深奥的各种层面的传统文化;不是将课堂教学作为传播深奥思想、体会细腻情感的传统文化的唯一途径,而是需要开发多种在非功利性的探讨感悟中提升人生境界的平台;不是大而化之地急于表达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激情,而是应该在担负起文化使命感的同时,宁静致远,从身边能够做好的一点一滴做起——正如我们国学社一位同学在读书报告中写到的那样:“我认为,学习国学的重点应在于理解、感悟并用筛选性的眼光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将传统与现代的精华相融合,激起有识之士从内心发出的对美好、对理想的追求与探索的热情。这或许不是一件可以速成的事,经过实践的过滤沉积,一定会有执着于理想、愿意奉其一生于真理事业探寻的人坚持下来,他可以感染一个人、一群人甚至一国人,直至国学、或任何一门学问得到优秀文化理当获得的普遍尊重为止。所以学习国学,要保持一颗好奇与敬畏共存之心,对于实践中的痛苦的担当,应当如对喜悦的渴望,需要以赤子之心坦然面对——沉静,是必须具备的品质。”
继续阅读
- 暂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