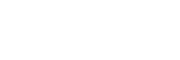什么是恐慌?科普:我们为何会恐慌

自从新型冠状病毒开始在全球肆虐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人们为了买到一卷卫生纸、一瓶洗手液或一只口罩会付出多少努力。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数量的增加,各州和各国纷纷关闭大型集会和商店,以扩大社交距离,这些不确定性正在引发所谓的“恐慌性抢购”,导致商店货架上的商品被人们迅速地一扫而空,商店都来不及补货。
至少从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爆发的时候开始,恐慌性抢购物资便成了人们应对流行病造成的不确定性的一种方式,当时,美国巴尔的摩的居民纷纷闯进药店,寻找一切可以预防流感或缓解流感症状的东西,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 2003年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爆发。
“人们出现极端反应,是因为人们感到自己的生存受到了威胁,需要做些什么来使自己获得一种‘一切尽在掌握’之感。”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精神疾病流行病学教授卡蕾斯坦·克嫩解释道。
但究竟是什么使我们陷入恐慌,我们又如何在遇到全球性大流行病之类的巨大压力时保持冷静呢?这取决于大脑的不同区域如何配合。
人类的生存仰赖恐惧和焦虑,要求我们在遭遇威胁时立刻做出反应(想象一下 :即将出现一只狮子),还要能够仔细斟酌已感知到的威胁(今天晚上狮子会在哪里?)
当大脑中的某种沟通出现异常时,恐慌就会产生。克嫩解释说,大脑的情绪中心杏仁核希望我们立刻摆脱伤害,但它并不关心我们如何躲避狮子。
然而负责处理行为反应的前额皮质则坚持认为,我们应该首先充分考虑狮子的情况。我们什么时候可能再次遇到狮子,到时该怎么办?
有时焦虑会成为障碍。
前额皮质并非与我们大脑中那些擅长规划和决策的部分直接沟通,而是受到大脑其他部分之间互相交流的干扰,这些部分会把我们如何变成狮子晚餐的所有可能性都模拟个遍。
当整个思维过程出现短路时,恐慌就会产生。我们的前额皮质想要思考明晚狮子会在哪里时,我们的杏仁核却在超速运转。
“当大脑中更为理智的部分[前额皮质]被情绪所左右时,恐慌就会出现。”克嫩说。恐惧感十分强烈,于是杏仁核支配一切,肾上腺素也开始分泌。在某些情况下,恐慌可以救命。当我们马上就要被狮子袭击或被汽车撞倒时,最理性的反应可能就是逃走、搏斗或一动不动。我们不希望大脑花太多时间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
但若是只听杏仁核的就会带来严重不足。社会学家恩里科·夸兰泰利对人们在灾难中的行为方式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在其 1954年的著作《恐慌的性质和条件》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名女子听到爆炸声,以为是炸弹击中了她家的房子,于是从家中逃离。直到她发现爆炸发生在街对面时,才想起来她把孩子落在了家里。
“恐慌不是反社会行为,而是一种非社会行为,”夸兰泰利写道,“这种社会规范的瓦解……有时会导致最牢固的基础群体关系破碎。”
恐慌对于应对长期威胁也没什么帮助。在出现长期威胁时,前额皮质仍需保持控制,提醒你可能存在的威胁,同时会花些时间来评估风险并制订行动计划。
但如果说我们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间接收到了大量的信息,那为什么还有人囤积卫生纸和洗手液,而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无视这些风险,还去酒吧聚集呢?
众所周知,人类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不善于评估风险,而且我们在评估时往往会犯各种错误,导致我们高估或低估了自己的个人风险。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副教授索尼娅·毕晓普从事焦虑如何影响决策方面的研究,她表示,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间,这一点便显得尤为正确。
来自政府、媒体和公共卫生部门的信息不一致(例如关于社交距离的各种建议),加剧了人们的焦虑情绪。“我们不习惯生活在各种可能性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毕晓普说。
她说,理想的情况是,我们应采取一种叫做“无模型学习”的方法来评估我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要承担的风险。这种方法本质上即为试错法 :我们依赖自己的个人经验,并逐步更新我们对某事发生几率的估计,如果它真的发生了,情况会有多糟,以及我们需要投入多少力量来防止它发生。
毕晓普说,在我们没有关于如何应对威胁的模型可做参考时,很多人会转而谋求“有模型学习”,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我们要么努力回忆过去的例子,要么模拟未来的可能性。
因此,“可得性偏差”就会悄然出现。当我们多次听说或读到某事时,例如一起被媒体广泛报道的飞机失事,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象自己坐在一架即将坠毁的飞机里,因而可能会高估飞行的风险。“正是由于模拟这种场景很容易,因而影响了我们对可能性的判断。”毕晓普说。
同样地,有些人对乐观和悲观也有偏差。悲观者会不停地满怀焦虑地想象世界末日所有可能的情景,而乐观者则倾向于相信不会有坏事发生。
即使他们都属于易受伤害的群体,他们也会从他们的世界观出发,找到一种方法来说服自己相信,自己非常健康,不会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这样做会让人们重新获得一些掌控[之感]。”毕晓普说。
恐慌有没有好处?虽然肯定会有人处于这两个极端,但大多数人却会有其他的体验:极度焦虑。在灾难面前,一定程度的焦虑是有好处的。
恐惧会成为一种动力,提升我们的警觉性和精力,提醒我们洗手、关注新闻,是的,甚至还有去杂货店囤积生活必需品。
特拉华大学流行病学创始人、公共卫生防备专家珍妮弗·霍尼指出,在美国这样的地方,恐慌多一点可能会特别有用。
在遵守隔离和检疫等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方面,美国人历来没有其他国家的人做得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多一点恐慌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行为确实会影响他人。”她说。
而在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焦虑很可怕。首先,随着我们变得更加焦虑,我们的大脑也很难不陷入恐慌模式。研究表明,长期的压力确实会使我们大脑中帮助思考的部分缩小,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人们的恐慌情绪。
毕晓普指出,我们的身体生来就不能适应连续数周或数月的巨大压力和焦虑。尽管压力和焦虑能在短时间内使我们的精力高涨,但最终却会让我们筋疲力尽、情绪沮丧。如果人们不再在意社交距离,在疫情到达顶峰之前又开始外出,这终将给社会反应造成严重影响。
在 2009年的H1N1(“甲流”)全球大流行期间,霍尼培训了多个快速反应小组用以应对疫情。她说,减少不确定性是确保我们的干预措施能切实发挥作用的关键。
她强调,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并非一无所知。公共卫生官员也在应对 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过程中对冠状病毒有了很多了解。
“许多正在进行的事情都是典型的公共卫生措施,我们用以控制疫情的爆发 ;只不过这次疫情的规模要大得多。”霍尼说。
“为防控疫情,我们一直都对邮轮进行检疫,但那些通常都是诺如病毒或季节性流感。”